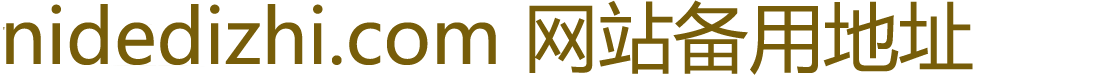
Swallow
细密的雨小了,几乎几乎听不见雨声,她也像刚从外边大雨里回来,浑身湿透,头发粘着汗,双目无神地盯着病房的天花板。
&esp;&esp;她只隐约记起手术室的冰冷,但江猷沉穿手术服出现在那,打着麻醉的她,以为自己精神分裂,哥哥远在美利坚才对。而医生护士给他让位,江猷沉给她穿袜子。她切实感到了,他手掌握住自己脚心的感觉,那热度传递过来,溢满整个冰凉的脚底。
&esp;&esp;赤脚踩在岩浆上一般。
&esp;&esp;在医院,她唯一可以得到满足的诉求就是打电话。
&esp;&esp;她打电话给江猷沉,想问,哥哥你是不是在北京。哥哥现在在北京或是中国的话,那之前出现在手术室的确实是他,而不是自己的错觉。
&esp;&esp;江猷沉接电话,声音干且哑,“怎么了?”
&esp;&esp;江鸾说,“您在睡觉?”语气变得难以捉摸起来。
&esp;&esp;“嗯。”他忽然深呼吸了一下,像从睡梦醒来时提起精神,伴随微微清嗓子声,并有从床铺里起来的声音,“吃午饭了么?医院给你吃的什么?”
&esp;&esp;江鸾沉默了片刻,然后如是回答。
&esp;&esp;江猷沉“嗯”了,似乎彻底放心了。
&esp;&esp;他彻底放心,江鸾知道,什么东西又要断开了。
&esp;&esp;“江鸾?”
&esp;&esp;“嗯?”
&esp;&esp;“你刚才在发什么呆?我再说一遍,”江猷沉声音非常平静,“你的治疗师在等你,他不会转介你。”想了想,他又说,“这是我和诸伯然医生共同的想法。”
&esp;&esp;“我在手术台梦到了你。”她忽然笑道,“哥哥,我应该给精神病院主治医生还是诸伯然说?我似乎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症状。”
&esp;&esp;那边沉默了半响。
&esp;&esp;江猷沉仔细地听着,她叫诸伯然不叫医生,直接叫名字。
&esp;&esp;“那是我给你穿的袜子。”
&esp;&esp;江鸾的声音忽然变了调子,“不可能,你在——”
&esp;&esp;江猷沉笑了笑,语气带一种强烈的安抚,“我当时在新加坡,正和人谈合同。聪明孩子,下次打电话给我之前,你先让医生帮你查查新闻?”在江鸾应声之前,他又说,“我刚接电话,就听说你差点砍断自己画画的右手。”
&esp;&esp;“……”
&esp;&esp;“可是那颗子弹——”
&esp;&esp;江猷沉没反应过来,问,“哪颗子弹?”
&esp;&esp;爸爸的清洗活动那一年隆冬。
&esp;&esp;江鸾声音带着急切,“我看到了,老宅闭关前进来最后一辆车的防弹玻璃上——”
&esp;&esp;“好了,好了。”江猷沉忽然打断她的话,对于这件事,江鸾第一次和哥哥提的时候,哥哥就有些讳莫如深。那种讳莫如深的态度使得一切更不可捉摸了。
&esp;&esp;“江鸾,”江猷沉声音平静而低深唤她的名字,“不管真的还是假的,我们都会爱你的。我们永远是一家人。”
&esp;&esp;“……”江鸾微微压下眼睫,聚焦着朦胧和光亮。
&esp;&esp;她好像还听到哥哥说,不管发生什么事,我们都会在一起的。
&esp;&esp;我们是谁,是她和江猷沉,还是她和爸爸妈妈哥哥,还是她和玉渊潭和南京。
&esp;&esp;在她沉思时,江猷沉忽然又换了另一个明朗的大人的声调,平稳、舒缓、宽和,“你明白了吗?”
&esp;&esp;“我明白了,”她语调平淡,表情生漠,声音尚且带着童稚的声线,“我不会和其他人说的。”她声音更加平静下去,“那时,之前,之后,未来都没和除你之外的人说过。”
&esp;&esp;江猷沉那边顿了两秒,方才传来笑声,“是个心底深的聪明孩子。”
&esp;&esp;电话由他挂断了。
&esp;&esp;她穿着白衣,躺在完全没办法伤到自己躯体的,软塑材质包裹的墙壁。
&esp;&esp;看到窗外天空的芝麻一样远走的燕群。
&esp;&esp;那之后,她再也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。
&esp;&esp;在医院,她唯一可以得到满足的诉求,还是只有,打电话。
&esp;&esp;她想去河岸边写生了。
&esp;&esp;河岸边四周草丛茂密拔高,坐下来时,就会发现腿上有浅浅的划痕。那些伤口结痂以后是一串小小的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