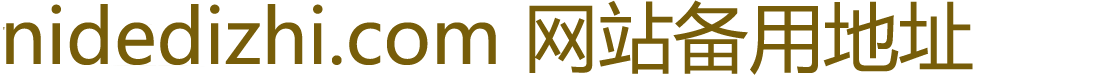
一旦说chu去名声尽毁(2更)
&esp;&esp;床帐挂起来了,浓稠的月色直照她身上,雪肤黑发渡着层淡淡银光,那双红红的眼圈儿,紧张地看着他,“我不要就是了”
&esp;&esp;张鹤景蹬上靴子,顺手拔下自己髻上的白玉簪给她。
&esp;&esp;簪子有定情之意,非比寻常。
&esp;&esp;要是收下,活命的交易岂不成了偷欢的私情?
&esp;&esp;江鲤梦不想同他扯上丁点儿关系,绞尽脑汁找出个借口,“我手笨,用不惯玉的,怕折。”
&esp;&esp;不擅长撒谎的人,心里打什么算盘,都会显在脸上。张鹤景不戳破,唇角扬起冷笑,“匣子里还有几十根,随便你用,断到明天早上也不怕。”
&esp;&esp;他语气轻飘飘的,四两拨千斤。
&esp;&esp;江鲤梦咬咬牙,还是接了过来,绾着头发,暗恨他怎么这样坏!
&esp;&esp;头发束好,她穿上鞋想站起来,两条发软的腿不听使唤,脚踝也疼得厉害,根本没法走路。
&esp;&esp;正为难,有条手臂及时横过来,二话不说把她抱起来。
&esp;&esp;她最没出息了,只会搂住他脖子。
&esp;&esp;他忽地轻“嘶”一声,停住了脚步。她犹如惊弓之鸟,怯怯问:“怎么了?”
&esp;&esp;张鹤景皱着眉,垂眼看她:“手松开些。”
&esp;&esp;她哦了声,松开手才发觉自己勒到他伤口了。往他脖子那边使劲瞅,勉强看到点外翻的皮肉。白皮红肉裂着口子,上面还粘着灰白粉末,格外狰狞可怖,她倒吸凉气,“你疼吗?”
&esp;&esp;张鹤景心头一顿,曼声道:“流了三盆血,你说疼不疼。”
&esp;&esp;江鲤梦虽内疚,却也不是蠢,“错不在我。”
&esp;&esp;错不在她,好像也不在他。
&esp;&esp;这场无妄之祸,本可以避免的,谁让她大半夜不睡觉出去乱逛,一头撞上。
&esp;&esp;女子没了名节,等同没命。设身处地,换作是她,她也会拼尽一切手段维护母亲,杜绝后患。
&esp;&esp;她可以怪他心狠,却不能恨他无情。
&esp;&esp;罢了,罢了。已经到这般田地,再懊悔,不过徒增烦恼。
&esp;&esp;牙打落了,就往自己个肚里吞吧。
&esp;&esp;权当是场噩梦。等梦醒,天也该亮了。
&esp;&esp;明早太阳出来,她还是她,没少胳膊,没少腿,能平安活着就很好了。
&esp;&esp;江鲤梦悄悄揾掉眼中泪花,听他说,“出了这个门,全都忘掉。”
&esp;&esp;“嗯”
&esp;&esp;她抬手去抽门闩,外面突然传来由远及近的脚步声。
&esp;&esp;江鲤梦愣住,睖睁着眼,看着窗屉映上个修长人影,缓慢地从门前走了过去。
&esp;&esp;紧接着隔壁的门“咯吱”一声。
&esp;&esp;“张钰景。”他似乎嫌她不够恐慌,还把那个名字说了出来。
&esp;&esp;江鲤梦扭过脸看他,眼中惊惧要溢出来,如临大敌,“怎么办?”
&esp;&esp;夏季门窗糊的纱都轻透,仅隔着一扇门,屋里能看外面,外面自然也能见里头。
&esp;&esp;只要不是瞎子,打从门前走,都能看到屋内站着两个人。
&esp;&esp;她开始发抖了,牙齿都有些颤,勉强抑制住,急赤白脸道:“你倒是说话呀!”
&esp;&esp;张鹤景静静审视她过于激动的脸,这般在意,一旦蒙混过去,“清白”的她,难道不会放心大胆的为张钰景泄露秘密吗?
&esp;&esp;“二哥哥?”他久未答言,江鲤梦急的满脸通红,搂着他肩膀使劲摇,企图摇回他丢失的良心,“怎么办呀!”
&esp;&esp;“别摇了,”他头晕脑胀,疲于再思考。
&esp;&esp;江鲤梦赔着小心,放和软声气:“二哥哥,你不能不管我呀。”
&esp;&esp;张鹤景哦了声,转身抱她回到里间,单手取下衣架上的披风,把她从头到脚罩住。
&esp;&esp;江鲤梦在衣裳底下发出不可置信的疑问:“就这样?掩耳偷铃?”
&esp;&esp;“既知道是偷,就低声些。”
&esp;&esp;他边说边推门出去,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,她悄声问:“你就不怕吗?”
&esp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