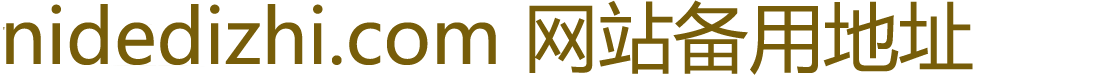
11 是福祸
<h1>11 是福祸</h1>
段沉沉接连三个月不眠不休的工作。
之前在跃梦唱一晚上是两千块钱,如今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,也不过两百出头的工资。
那天她收拾东西从段浮浮的出租屋离开,她坐在一边擦指甲油,本就不大的房间里混杂着潮气和劣质的指甲油气味。
她看段沉沉的眼神就像是小丑胡闹,眼眸不抬,语言轻浮:“你说你这是何苦呢,就当因祸得福不行吗?”
什么是福什么是祸。
段沉沉早就分不清了,她张不开嘴,毕竟被段浮浮打到破裂,稍稍用舌头润一下,都疼的不行。
两件旧外套,三条泛白的牛仔裤装箱。
“你之前唱歌一天才赚两千,现在只要你肯找活,一次起码这个数。”
她涂的是什么颜色的指甲油呢。
好像是宝蓝色,有些沾到了死皮上,并不好看。
两块宝蓝色在段沉沉面前晃了晃,光线昏沉,她头晕眼花,生理的不适让她险些呕吐出来。
段浮浮无语了。
她看着拖着箱子要走的人叹了一声气,警告道:“你要走可以,我会跟追债的那些人说债务我们平摊,你一个月还三万。”
箱子底下的万向轮似乎坏了一个,怎么拖都是迟钝的。
门打开,段浮浮自言自语,也不在乎段沉沉能不能听到:“真弄不懂你,躺着张开腿就能赚钱,非要去干苦力。”
门关上,万向轮在下楼时撞掉一个。
段浮浮又说:“走了可别回来了。”
医院的广播循环叫喊着。
等诊的病人们不约而同四处寻找广播中的人。
段沉沉高烧不退,三个月内第一次请了假,她觉得再这么下去,自己可能是要死了。
冬天将至,女孩缩在角落颤抖,状态昏迷。
医院的椅子都是铁质的,不知为何,椅子上还会布满一个个小孔,段沉沉手心撑在上面,皮肤上起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小孔印痕。
她的名字消失,有人坐在距离一个空位的地方。
任谁都看的出这个女孩很不舒服,却没有人来询问一句,人心冷漠。
这是梁从欲很小就明白的道理。
空一格的位置是礼貌,他转过头,五官温和,声音也很好听。
“小姐,你还好吗?”
段沉沉介于昏迷与熟睡之间,叫很难叫的醒,她感觉到有一只冰凉的手放到额头,她快要起火的那个地方,这种温度让她舒适不已,更加不想醒来。
梦中身子似乎变得轻盈,她以为是自己的灵魂在离开身体。
一边想要为死亡哭泣,一边又为解脱感到高兴。
她晚上醒来。
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狱,冰冷的病床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
神态很散漫的小护士走进来,检查一番她的身体,话说的着急,“再观察一晚上,明天不烧了就可以出院了,来,你的药。”
那不是她花钱买的,医院也不是慈善机构。
段沉沉嘴唇干涸,死皮张牙舞爪的凸起,“这些多少钱?”
她问。
“不要钱,你的朋友给你买的。”
“哪个朋友?”
护士的眼神变了,“男的,你不认识吗?他说他姓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