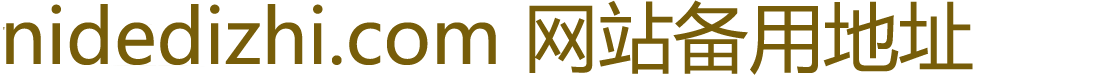
12 我妹妹
<h1>12 我妹妹</h1>
梁从欲献完血回到关颐楼时天刚黑。
其实也不过五点钟。
他在工作台旁看到祝念,猛的发现她的头发长了很多,到了腰,不知道用的什么洗发水,又黑又直。
抬脚企图靠近一步,祝念整理好今天完成的单,抬头就看到了梁从欲,她笑了下。
梁从欲又想到今天在医院遇到段沉沉。
奇怪,她的头发好像没有长,还是在跃梦时的那个长度,很软,带些自然的微卷,祝念跟她可不一样。
叹了口气,他转身走了。
留下一个姓,以后每每段沉沉遇到姓梁的人都会猜想会不会是那天帮自己的人。
这样的念头循环绕了几天。
港京初雪那天段沉沉在路边的包子铺买了一个豆沙包和一个茶叶蛋。
笼屉掀开时白色的浓雾迷了眼。
蒸的她热泪盈眶,谁会为一个包子流泪,真是穷傻了。
小雪而已,她没有打伞,递给老板十块钱,却只找了五块。
不禁感叹最近物价疯涨的厉害,吃一个包子可不是要流泪吗?
走到工作的药店门口,段沉沉的双脚已经冻的生疼,她出走时一双鞋也没有带,也没有时间去买,一双浅口板鞋穿了几个月,最近在叫嚣着罢工。
站立了下,门被从里推开,凸起的把手撞到她的关节骨,拎着包子的手条件反射的撒开。
这回,她是真的要流泪了。
雪白的包子滚出塑料袋,胖乎乎的身子上粘了雪,不漂亮了。
“不好意思,我赶时间。”
女孩手里拿着两盒金嗓子,慌忙跑向路边的豪车里。
女孩,金嗓子,脏了的包子,这是开端。
那之后接连一个月,那个女孩都会来药店,每次买的东西都不一样,却照例钻进那辆豪车,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。
慢慢的,药店的员工开始讨论她。
未知的是那辆车里坐的是谁,买那些乱七八糟毫无用处的药是做什么,只要能拿出来打发时间,他们都能聊上很久。
段沉沉也是普通人,自然也有好奇心。
直到那一天,暴雪。
女孩没有来,来的是豪车的主人。
轮到段沉沉值班,她坐在收银处,低头发呆时陌生的黑影给玻璃柜台带上一层颜色。
“你好……”
梁从欲穿着灰色的高领毛衣,将脖颈线条拉长,文质彬彬,他礼貌地应道:“你好。”
这么久的时间,他在猜测段沉沉能不能认出他来,毕竟在跃梦,他们见过。
可惜看样子她似乎没有半点记忆。
“需要点什么吗?”
这里是药店,梁从欲否定的摇头,忽然将手上提着的一大袋药品放上来,盖住了段沉沉的脸,她坐的椅子矮,只露出一个脑袋。
梁从欲往边上挪了挪,解释道:“我妹妹之前在你这儿买了很多药,不知道能不能退?”
这种无理的要求,连他自己都觉得好笑。
段沉沉不明所以,慢吞吞地指了指柜台边角的温馨提示:药品一经售出,概不退换。
梁从欲当然知道,“那能请你帮我算一下,这些药一共多少钱吗?”
段沉沉歪了下脑袋,没有动。
梁从欲说:“我一个月之前去医院,她还以为我生了什么病,就每天花钱乱买药,零花钱都花光了。我说要给她钱她不肯要,很自责,所以我想知道这些花了多少钱,我好跟她说是退了药换来的。”
女孩买的药什么品种都有,治头痛的,胃痛的,消炎的,每天都买。
怎么着也有好几千了。
眼前这个人明显是想得到一个确切数字,好让妹妹高兴。
考虑完,段沉沉打直僵硬的膝盖,“那你等一下。”
药店没有计算器,她只能拿手机一个个来算,这些药品种杂,有些根本就是夹角旮旯里放了很久的冷门药。
她也未必就全部记得价格,全部核对完毕已经很晚。
本来就是值夜班,九点下班,被这单不赚钱的生意拖慢了半个小时,如果不是男人眼神赤诚,她恐怕要觉得他是诚心来刁难的。
算账的过程缓慢,梁从欲一动不动站在柜台前,盯着段沉沉的手指在手机屏幕的数字上游走。
她的甲型生的美丽,修长又带着点健康的粉白,形状修剪的刚刚好。
“是不是打扰你下班了?”
梁从欲将目光从她的手指放到额头,美目波动了下,段沉沉忘记了手下这盒药多少钱,“一点。”
她这么说。
“你带伞了吗?”
梁从欲问。
外面又下起了暴雪,落在脸上一定是寒冷又疼痛。
段沉沉不明白他这么问是什么意思,在跃梦时自带的对